本篇文章3172字,读完约8分钟
这次危机爆发以来,我们思考了这场危机可能持续的时间、可能发生的深远的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 从2010年开始,我们开始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快速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这些机构都完成了非常出色的报告,本文是该研究的总报告。

二次危机的共性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着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总结两次危机的共同点。 初步得出十分结论,简要说明如下
一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都是在发生了重大的技术革命之后。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发生重大技术革命后,不仅要认识其进步作用,挖掘其带来的机会,还要充分意识到将会出现重大变革,充分估计振动影响和挑战。

2 .危机爆发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采取了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两次繁荣期间,经济自由放任与公司创新精神的发扬相辅相成,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之后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逻辑关系。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优势是,相对少数的人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 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的名义所有权与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在虚拟经济行业的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 .在公共政策空之间受到小压迫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一般是危机的推动者。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带来的心理压力,常常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执政期间无法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因此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民粹主义政策宣言,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改变了大众福利的期望,提高了对政府的依赖,放松了自己奋斗的决心,效果是极其负面的腐蚀剂。 致命的问题是,群众福利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就会逆转,形成轻视权威、拒绝变革、憎恨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而且,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地成为习性,这种习性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充分表现出来。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相信自己能一夜致富的理由。
二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中出现的巨大差距,常常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发生变异。 其改变社会地位的迫切心情,迫使大众开始追求一夜之间的财富,人们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能经受得住泡沫产业的诱惑……正如加尔布雷思所说,经济过度繁荣的时候, 人们不是找理由让自己理智,而是找理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六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有关。 在两次危机之前,最便利的手段是采取更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发了股市泡沫和投机狂热在此次危机前,联邦储备系统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宽松监管和次级贷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使泡沫恶性膨胀。

7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的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市场力量持续挑战没有说服力的政府政策,使危机局势更加恶化。

在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政策上总是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总是错过时机,应该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采取紧缩政策,应该进行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时候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压缩社会福利,推进结构改革的时候是困难的,反复后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事后看起来很奇怪,但对当事人来说很难实施正确的政策。 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只会遭遇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面临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经济问题政治化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舆论绑架,被政治进程锁定,不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这是呵呵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市场在两次危机中的力量始终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 如果只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忽视政治属性,就会犯严重的评价性错误。
8、危机快速发展有特定的发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扩张的逻辑之前,经济复苏不可轻言。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事故。 他们好像有点概率的事。 由运气决定。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旦经济从正常状态过渡到危机状态,它就会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开始循环。 危机始于经济的大幅跳水,从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上升,从经济困境恶化走向社会矛盾激化,大多从经济社会行业转移到政治行业乃至军事行业。

目前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的实现过程中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经常发生。 当前,欧债危机不断深化,中东局势不明,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对此次危机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9 .危机只有迅速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能推出比较有效的处理方案,这个处理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之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 这次理论创新有可能围绕世界经济最实质性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上发生的总诉求萎缩和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之下,加上一点点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困境,带来了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如何将这个问题迅速传播到全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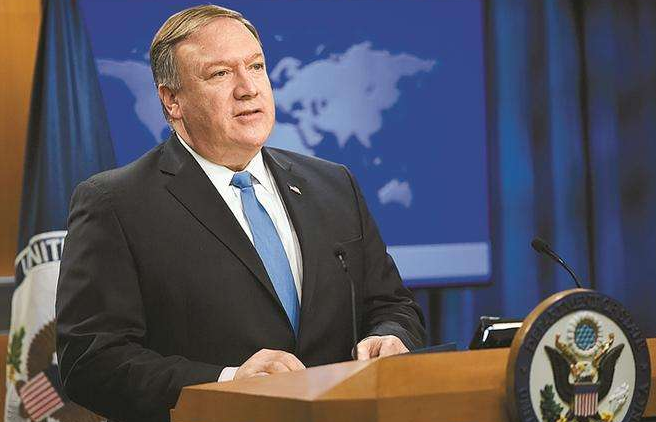
10、危机具有很强的再分配效应,会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会再次得到验证。 基辛格在他的名着《大外交》中向宗明义指出,世界每100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大国。 这次危机发生后,世界快速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诞生了二十国集团( g20 )平台,世界实力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不仅对生产力快速发展有破坏作用,还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有更强的再分配效果。

三种政策性思考
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思想成果,受到了很多启发。 考虑到我国加快经济快速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众多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中,我想首先提出三点思考。

1 .对可能发生危机的最坏情况,确立底线的想法。
的结论与当前欧洲债务危机加速恶化的情况进行比较,必须建立底线思维的思想途径,为危机状况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更好的结果,这就需要做好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荡的长期准备

目前,有两个场景需要预防:一是危机升温带来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将灾难转嫁给一点国家改变形态的战争。 这两个场景最近出现是很小的概率,但需要防患于未然。

2 .把握中国战术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与世界利益的最大交叉。
比较研究的结论也表明我国战术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经济意义上讲,在此次危机面前,中国的战术机遇主要是海外市场的扩张和国际资本的流入,中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此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诉求不足和杠杆化的漫长过程,中国的战术机会主要是国内市场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是发达国家展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中国和大国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巨大利益交叉,确定处理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确后,切实实施。

3、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牢牢抓住重大课题的实务先行研究。
比较研究结论还表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突出要点,扎扎实实地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建议对要集中力量搞好的事情进行更务实的研究,特别是要增强全世界的视野,提高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报告的课题组组长刘鹤是总报告撰写人刘鹤。 本文在形成初稿后,分别征求了吴敬琏、樊纲、易纲、李扬、韩文秀、卢迈、刘春航、魏加宁、蔡洪滨的意见,并征求了央财内部杨伟民、蒲淳、刘国强、尹艳林、赵建的意见。 作者衷心感谢这些同事提出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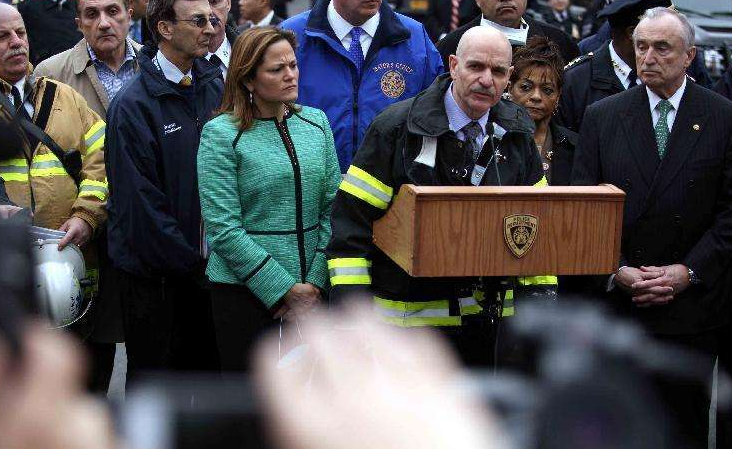
本论文是去年10月1日出版的《比较》
标题:“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地址:http://www.9u2j.com/wnylyl/204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