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1306字,读完约3分钟
2009年2月28日至2010年4月15日,被告人徐谋谋利用其在甲方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职务,利用其控制的证券账户史谋谋亲自或通过电话指示张在他管理的分红基金和均衡基金中提前或同时买卖同一只股票。

据评估,上述期间共交易股票68只,交易总额超过9500万元,非法获利超过209万元。2011年4月18日,被告人徐某某主动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进行调查,并向公安机关如实说明了上述犯罪事实。

被告徐某在担任基金管理人期间,违反国家规定,利用未披露的信息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多次或同时买卖同一只股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犯罪,应依法惩处。被告人徐谋谋自首,为初犯。在审判期间,他偿还了所有的非法收入,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忏悔,他不会再伤害社会。他可以根据法律和自由裁量权被从轻判处,并可以被停职。判决如下:1 .被告人徐谋谋犯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10万元;2.被告徐谋谋返还的赃款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本案中,对被告徐某某的指控以及被告徐某某在信息公开前从事同一股票交易的事实没有争议。但被告人徐谋谋的辩护人认为“68只股票并未因徐谋谋的行为而出现异常波动”。从刑法的构成要件来看,无法从上述事实推断其证券交易是“使用”未披露信息,也无法证明客观行为与未披露信息之间的关联程度。

基于此,笔者将对“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罪中的“利用”的“刑事推定”原则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利用”的必要性。一方面,它在于法律基础的逻辑框架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利用”一词表示交易行为和未披露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实际上不是利用未披露的信息进行交易,而是按照既定的规划流程,辅以自身的分析和判断,是一种合法的交易行为,不会造成证券期货市场的健康运行。刑法的介入违背了谦抑性的概念,扩大了合理的规制范围。

其次,很难证明“利用”。与传统犯罪相比,金融犯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抽象性,行为模式和主观目的的认定比自然犯罪或其他简单的法定犯罪更加困难。此外,互联网已经突破了犯罪行为发生的空场和时间场,因此如何确定市场主体确实影响了市场的规则和正常运行是值得考虑的。因此,当不能获得被告对“利用”的承认时,根据其他证据形成的链条推定“利用”的合理性。

与“推定”相对应的是“反驳”。简而言之,“刑事推定”可以理解为在基本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建立正常的关系,这是极有可能的,而“反驳”则是推翻这种经验解释和可能承认的范围。例如,在上述情况下,首先,交易的股票种类相同。分红和平衡基金买卖的股票品种与被告徐谋谋买卖的股票品种一致;第二,交易的时机是相关的。当然,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投资判断是基于已公布的数据等信息”或“通过对操作规则、经验规则和证券期货的了解,确定交易的股票品种与未披露的信息无关”,则“利用”的推定无效。

因此,笔者认为在证券期货领域严重的“内幕交易”下,利用管理岗位上大量未披露的信息侵害投资者的行为应该上升到刑法规制的高度。有必要对此类犯罪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争议难点进行解读,这有利于优化司法认定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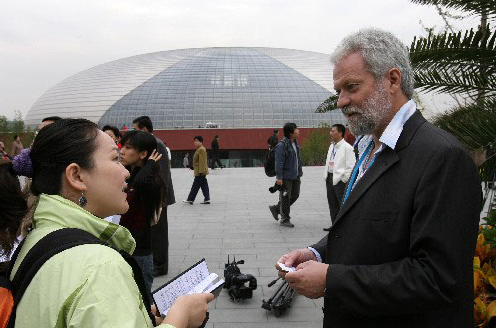
(作者: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标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中“刑事推定”规则
地址:http://www.9u2j.com/wnylyw/13818.html

